“朱子与闽南”文化论坛
暨第五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在漳州举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我市朱子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部署要求,从新的视野深入研究朱子与闽南文化关系,进一步发掘朱子文化的当代价值,激活闽南文化特色资源,讲好闽南文化故事,推进两岸文化融合,2022年6月25日至26日,“朱子与闽南”文化论坛暨第五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在漳州古城向阳剧场举办。

漳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吴卫红,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事长刘宜民,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陈支平,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芳华,漳州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李珊珊,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龙海,漳州市关工委执行主任周亚冷等领导嘉宾及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
吴卫红在开幕致辞中强调,要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汇聚广大专家学者和朱子文化爱好者的智慧和力量,把朱子文化打造成具有漳州特色的文化标识,让朱子文化与闽南文化、海丝文化、侨台文化、红色文化相呼应,让优秀传统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奋力谱写富美新漳州建设新篇章凝心聚力,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论坛上,林晓峰作《论漳州是朱子理学南传重镇》主旨发言。他指出,朱子与闽南有不解之缘,闽南文化给年轻朱子以文化滋养,朱子理学又教化了闽南大地。朱子理学的发展有五个阶段性标志,分别是逃禅归儒、从学李侗、致力研学、初成体系、成熟体系。漳州是朱子理学南传的重镇,朱子知漳时,其思想体系已日趋完备,并具备推广理学思想的条件。他在漳主政期间实施仁政、践行理学、刊刻经书、兴教讲学、培育门人,其中高徒陈淳是朱子理学南传第一人,闽南理学家对朱子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作《郑成功对台湾儒学教育的影响》《朱子家训与范文正公家训之比较》《朱熹道统观的形成发展与漳州》《陈淳研究刍议》《黄道周与朱子学论略》《朱子与南宋地方治理研究》《朱熹泉州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考略》《论明儒黄道周从祀孔庙的历程及其意义》等主旨报告。专家们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分享了各自对朱子学及其在闽南传承发展的理解,观点新颖,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意义,深受听众喜爱。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分场研讨交流,深入研讨围绕朱子文化与当代价值研究、朱子与闽南文化研究、朱子理学思想研究、陈淳与朱子后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与此同时,本次活动汇集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各类相关学术研究论文近80篇。专家学者们通过研究纷纷认为,朱子理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实践、完善与多元一体的闽南文化息息相关,漳州是朱子理学南传重镇的观点赢得大家的认同。
朱熹理学思想主体来自儒家思想,来自多源广采博纳,来自社会民间。闽南是朱熹理学思想形成重要来源地之一,漳州是晚年朱熹主政之地,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之地,是朱子理学南传重镇。在历史进程中,朱子理学教化闽南大地,闽南沃土滋养朱子理学,闽南文化与朱子理学传播至海峡两岸,传播至东南亚,传播至世界各地。朱子理学是中华文明、东南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体现。

本次活动由中国朱子学会、中共漳州市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漳州市文旅局、漳州城投集团主办,闽南日报社、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漳州古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漳州城投古城运营有限公司承办,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中心、芗城区委宣传部、龙文区委宣传部、芗城区西桥街道党工委、漳州圆山发展有限公司、芗城区古城办协办。
据了解,自2012年6月以来,在中国朱子学会、闽南师范大学及国际儒联、厦门大学国学院、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等单位大力支持下,漳州市龙文区先后举办四届“海峡两岸朱熹陈淳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围绕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与漳州、朱子文化与台湾社会、朱子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朱子学与地方社会治理、朱子学与东亚朱子学、朱子学与闽南文化、陈淳对朱子学说的传承与发展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交流,共同探究朱熹陈淳学术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促进朱子文化活态传承,推进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0年5月,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与闽南日报社在漳州举办“朱子知漳830周年研讨会”,各领域专家学者交流分享了朱子与漳州、朱子理学与闽南文化、朱子文化与城市文明涵养、朱子文化进校园等方面内容,对朱子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当代价值、现实意义等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

近十年来,漳州朱子文化研究与传播不断拓展深化,相继出版《朱熹陈淳研究》《陈淳研究》《陈淳评传》《陈淳研究论集》《北溪先生全集》等专著;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相继推岀《朱子理学与闽南文化》《漳州是朱子理学南传重镇》等课题研究、专题讲座,产生很大影响;知名作家青禾创作的传记小说《朱子在漳州》,让漳州人走近朱熹,熟知他知漳所做的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今年来闽南日报社还组织策划了“寻访漳州朱子文化印记”大型新闻摄影采访活动,以梳理漳州朱子文化印记为主线,走访全市各县(区)选取相关史迹遗存,采用“新闻摄影+文字+短视频”的全方位报道形式,“行进式”呈现朱子在漳州的深远影响,深入挖掘朱子文化的当代价值,相继刊发10个专版,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由闽南日报社组织漳州朱子文化学者和中小学名师,在近十年漳州朱子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历时三年编撰的《漳州朱子文化》普及读本(分简明、初中、小学三册)也于近期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列入今年中小学生暑期课外阅读推荐目录,推进朱子文化进校园,帮助青少年学习了解朱子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专家发言摘要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林晓峰:
漳州是朱子理学南传重镇
朱子与闽南有不解之缘,他在闽南地区生活的时间长达八年,跨越童年、青年、老年三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朱子理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实践、完善与多元一体的闽南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说,闽南文化给年轻朱子以文化滋养,形成体系的朱子理学又教化了闽南大地,如今闽南地区尚留有众多的朱子理学遗存。
漳州是朱子理学南传重镇。朱子理学发展有五个阶段性标志,分别是逃禅归儒、从学李侗、致力研学、初成体系、成熟体系。朱子知漳时,其思想体系已日趋完备,并具备推广理学思想的条件。他在漳主政期间实施仁政、践行理学、刊刻经书、兴教讲学、培育门人,朱子理学思想在闽南不断实践完善。
陈淳是朱子理学南传第一人,“游其门者,天下居其半,独北溪传一派于南漳。”朱子的高徒陈淳终身致力于朱子学说的学习、阐发与传播,对理学思想第一次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解释,形成了朱子学的北溪学派,门人整理成为《北溪字义》并传播至闽南各地、闽地内外,代代相传,影响明清钦定教科书的内容,培养出后世一大批闽南理学家,如蔡清、黄道周等。
闽南理学家坚守朱子学统、一脉相承,推动朱子理学发展。宋元明清以降,朱子理学在闽南坚守正学,不断发展。明清时道学东传,近传台湾,传至日、韩、越等,远播东南亚。漳州由此成为朱子理学南传重镇。
目前“朱子与闽南”的课题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亟待更深入更广泛地挖掘与研究。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陈支平:
朱子文化研究在漳州硕果累累
朱子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朱子文化极大影响了闽南文化的同时,闽南文化对朱子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漳州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在很早之前就自发地开始了对朱子文化的研究,后来成立的闽南文化研究会,在闽南文化和朱子文化相融合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掀起了朱子文化和闽南文化研究的新高潮。近年来,闽南地区、特别是漳州的朱子文化研究氛围越来越浓厚,漳州举办的各类朱子文化研讨会功不可没。
在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漳州更将朱子文化推向教育、教化阶段。历时三年编撰的《漳州朱子文化》(分简明、初中、小学三册)普及读本近期陆续出版,我相信这将极大促进朱子文化在漳州传播,对于传承朱子文化有重要意义。希望在漳州各界专家、学者和闽南文化研究会的努力下,朱子文化的研究能够走向更高层次、更加深入人心。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荣誉指导,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首任馆长、研究员 杨彦杰:
郑成功对台湾儒学教育的影响
台湾儒学的兴起与郑成功有着密切关系。郑成功在金厦期间特别注重对儒家人才的延揽、储备、培养和使用,为台湾儒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在郑成功的人才队伍中,陈永华对台湾儒学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陈永华经王忠孝推荐,辅佐郑成功之子郑经建立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孔庙,兴办儒学,完成了郑成功的未竟事业。此外,郑成功时期的闽南文化氛围为台湾儒学教育注入了朱子学的内涵。明郑时期,闽南地区普遍崇拜朱子,把朱子学说奉为理学正宗。这样的文化教育取向自然延伸到台湾。因而,明郑时期台湾的儒学教育应被视为闽学入台传播的起点。当时台湾的儒学教育注重朱子学内涵,符合历史发展逻辑。清朝在台湾明郑孔庙的基础上建立朱子祠,便是这种历史延续的结果。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名誉顾问 谢重光:
朱子家训与范文正公家训之比较
范仲淹家训《百字铭》《训子弟语》、朱熹家训《朱子家训》,至今仍对炎黄子孙有重大教化作用。范仲淹家训突出“义”字,主旨在于纠正五代以来礼义沦丧之弊;而朱熹家训突出三纲五常,是理学占据主流的反映。范、朱两部家训共同的基本精神在于训诲子孙后代遵循儒家礼教。范仲淹家训强调“处世行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同样体现于朱熹家训中。而由于时代不同、个人性格和素养有异,范仲淹家训与朱子家训也有明显的不同特点:范仲淹重义,朱熹重礼;范仲淹信佛,朱熹信天命;而范仲淹强调的勤俭廉洁,朱子家训是比较忽视的。两位大儒的家训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将其理解透彻,认真整理、鉴别、吸收、扬弃、转化,承传其中的精义,是我们学习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工作。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 涂志伟:
朱熹道统观的形成发展与漳州
道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问题,自孔孟始,儒家思想便有道统意识。朱熹最早正式提出“道统”理论,其“道统”学说的形成、发展分为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阶段,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理论上撰文著书立说阐述;二是从学术上与友人、门人交谈或书信往来探究;三是从实践上支持各地修建官学、书院,祭祀理学先贤,撰记传播。漳州是朱熹道统观形成发展的重要转折节点。青年时期朱熹到漳州受到启发,初步开始道统溯源。中年时不断发展,从北宋诸先贤追溯至二程,再追溯到周敦颐,确定理学宗师,形成道学谱系。朱熹晚年时主政漳州,陈淳提出朱熹是天下道学宗师之说,朱熹沧州精舍释菜时承担起道统继承人重责。朱熹逝世后,漳州是全国最早在州文庙学宫立祠主祀朱熹之地。在朱熹门人持续努力下,朱熹从祀文庙,朱子理学成为儒学正统。宋元明清以降,漳州门生及闽南后学捍卫师门、形成学派、延续道统,儒家正学一脉相传,延绵不断,形成朱子理学鲜明的闽南现象。

闽南日报社总编辑 叶明义:
陈淳研究刍议
朱子学说凝聚了朱子及其门人弟子的智慧,是以朱子为核心,由朱子学派集体智慧和智能创造的成果。陈淳终生服膺朱子,潜心理学,是朱子最重要门人和衣钵传人之一。朱子学说博大精深,著述浩如烟海,能提纲挈领者实属难能。陈淳的独特贡献就在于穷尽一生把朱子的书“读透读薄”,通过综合萃取,对朱子理学的范畴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整理和解释。其代表作《北溪字义》,是一部浓缩了朱子学精华的杰作,是开启理学宝库的“密钥”,有“东亚第一部哲学辞典”之誉,为后人学习掌握朱子学说要义提供了便捷通道,对朱子学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陈淳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陈淳这一800年前闽南儒者,这一入祀文庙的闽南理学开创者,经过中国朱子学界和漳州文化界的持续研究与传播,正拥有越来越重要的一席之地,已然成为“闽南的朱子,中国的陈淳”。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黄道周与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郑晨寅:
黄道周与朱子学论略
朱子学发源于闽而走向全国、乃至海外,而在闽地,多有受其沾溉、熏陶进而对其进行发展、创新之学者,黄道周即为其中之特出者。朱子知漳是漳州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而黄道周则是其后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坐标。黄道周自幼读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历史价值观深受其影响;入仕后力主对内改良政治,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其学问博大精深、易学卓然一家,一生致力于讲学传道,既称朱子之学“百世无弊”,又加以发展创新,可视为明末理学之殿军。清光绪初年漳州知府沈定均在《增刊〈漳州府志〉序》中云:“(漳州)自宋朱子为之官师,洎明石斋黄氏以理学忠孝倡导后进,士民益敦志行。”此语一是指出朱熹、黄道周对于清漳一地教化之先导作用;二是将两人相提并论,揭示出黄道周对朱子的一脉相承。
结合漳州(闽南)的区域文化与明清易代的历史情境,基于朱子学视域,可窥见黄道周通过以《易》经纶天下、以“礼”治国齐家、以致知工夫对治时弊、以奉祀先贤重建信仰等诸多努力。

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闽南师大闽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刘云:
朱子与南宋地方治理研究
朱熹不仅是理学集大成的大儒,也是南宋一位在地方治理方面颇有贤名的官员。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推行治理措施时,能够以儒家思想结合国家法令,找到地方治理的关键点,申明朝廷法令,维护社会秩序,减轻百姓负担,兴办学校,推行教化,劝导百姓重视生产,讲求荒政,救济贫困,推广社仓制度,惩治贪官污吏,为南宋地方治理之清流,治理颇见成效,其治理模式为后世所称赞和借鉴。但是,在南宋逐渐腐朽的吏治背景下,朱熹的治理措施难免遭到一些朝廷大员和地方官吏、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其治理成效不容乐观,要具体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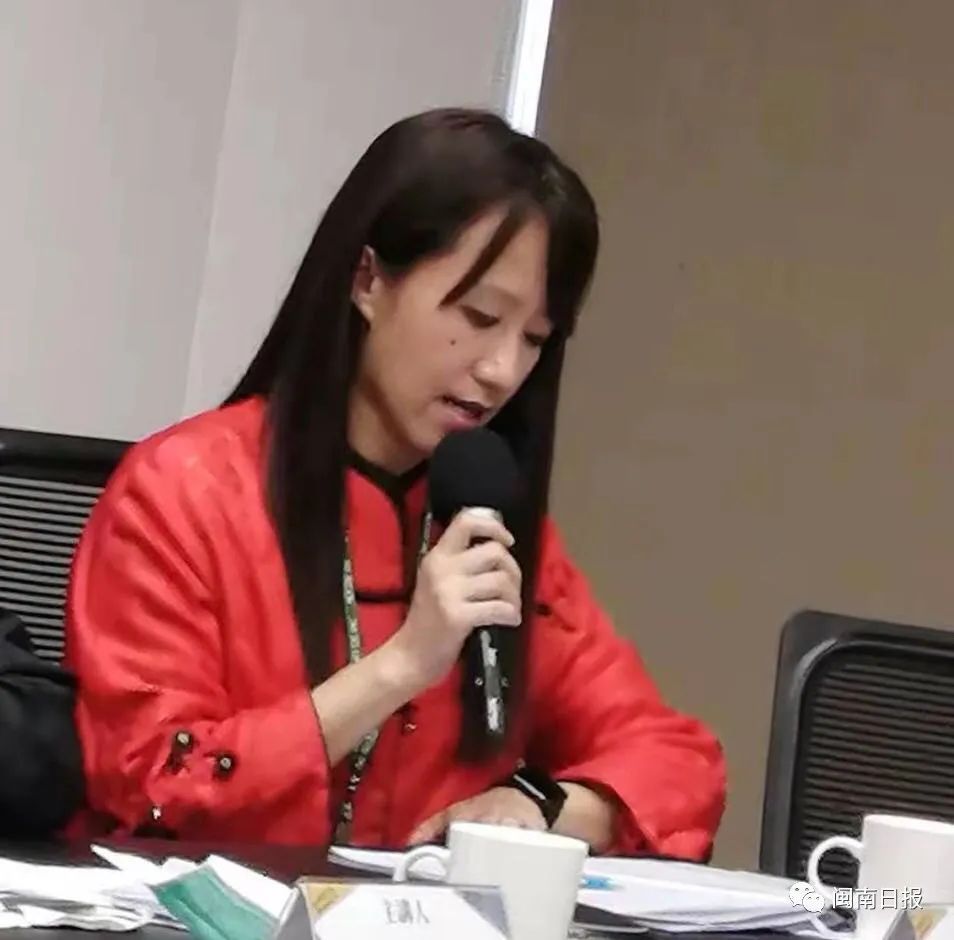
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蕙如:
论明儒黄道周从祀孔庙的历程及其意义
道光五年(1825),清廷旨准黄道周(1585-1646)从祀孔庙「西庑先儒」第34位,在明臣罗钦顺之次。黄道周的从祀不但是对其人地位的肯定,也凸显清廷对先儒定位的转变。经由本文探讨,获致结果有三:其一,地方人士对请祠确实有其贡献。作为抗清忠烈的黄道周,曾长期受清廷冷落,论史著作多被禁毁,到了道光年间能从祀孔庙,应与儒者陈寿祺的积极收集黄道周诗文,并多方奔走,联合当地仕绅,上书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准有关。其二,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即以程朱理学作为正统儒学,黄道周一向被视为朱子学者,其人传递圣学,以阐幽光,请祀的顺利也就在情理之中。其三,清廷重视通过表彰明末殉节诸臣来笼络人心,巩固其统治。

泉州师范学院教授、中华朱子学会理事 林振礼:
朱熹泉州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考略
朱熹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上看”这副对联,撰书时间地点不同,其动因及意蕴是有差别的。通过田野调查,将镶嵌在南安洪濑玉枕山清水岩后殿大门左侧的《重建清水岩碑记》,与泉州开元寺《广义法师舍利塔铭》进行觧读与互证,加以从地方志及文献稽考,得出的结论是:朱熹楹联撰书于淳熙十年(1183年)冬;瑞梁、广义师徒于1927—1928年重镌该楹联。文章认为该楹联书于淳熙十年(1183年)重游之际,既有地方志记其行踪,又有可视同手迹的存世题刻作证,故认为“可备一说”。
然而,历史的隐微之处扑朔迷离,治史忌孤证。作者自己也认为其所持的“泉州说”由于地方志书文献证据不足,说此楹联是淳熙十年冬朱熹与陈知柔一行同游杨梅山雪峰岩之际所书,需要佐以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漳州白云岩”之说有清代地方志记载作为支撑,文章对“漳州白云岩”之说表示充分尊重(没有一字非议)。同时认为漳泉两州之说都有可能出现“奇迹”,期待着新的发现。